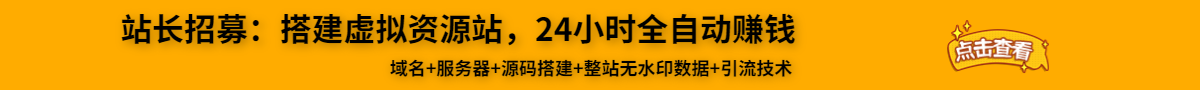限 时 特 惠: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,一年会员只需98元,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
站 长 微 信: qihangxm102

《雪祭》,一部荣获“五个一工程”大奖的现实题材小说,是作者党益民蘸着血泪写出来的赋情长诗,是书写边疆军旅生活的有温度的、有力度、有厚度的典范之作,是反映几代西藏军人激荡命运的史诗之作。书中有作者对战友、对时代、对国家深沉的感情,有喧嚣时代中深挚的担当。
中国军网微信将陆续刊发小说《雪祭》中的精彩章节。谨以此向全体战友,向所有边防军人致敬!
(二十三)
刘德厚老人躺在关中一铺土炕上,回忆三十多年前他在风雪中掩埋妻子王丽云的时候,另一对男女军人即将遭遇另一场暴风雪。

雪拉山半腰上的乌云很沉很厚,即使山谷里刮上来的硬风也无法将它们吹散。他们行走在雪线之上,夜幕已经提前降临。乌云突然压下来,挤走天地间最后一丝光亮,暴躁的山风变得异常诡异,打着旋儿在乌云里左冲右突,仿佛关在笼子里的野兽。赵天成闻到了雪的气息。看来暴风雪真的要来临了。
今晚麻烦大了。我怎么没有听“小钢炮”的劝阻留在六连呢?为了躲避黄雪丽这个麻烦,却将自己和黄雪丽一起带入了更大的麻烦。但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,掉头回去显然来不及了,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。他扭头对黄雪丽说:
“黄医生,咱们得快点走,暴风雪就要来了!”
“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!”
黄雪丽喘息着说过这句话,仍然低头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她显然是在故意气他。一路上,他有意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,这让她很生气。暴风雪快点儿来吧,越猛烈越好,我才不怕呢。这么想着,她索性停下了脚步,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。赵天成急忙返回来问:
“你咋啦?”
“我走不动了。”
黄雪丽耷拉着脑袋,坐在那里喘息着。她不只是在赌气,是真的走不动了。海拔5000多米,已经走了七八公里,她确实太累了。

“不让你来,你偏不听!现在不逞能了吧?”
“你不也逞能吗?说不会有暴风雪,现在呢?”
赵天成蹲在她跟前问:“真走不动了?”
她在黑暗中白了他一眼,没有说话。他扭过身子,背对着她。
“你干嘛?”
“少废话,快上来!”
“这样不好吧?”
她嘴上这么说,心里却在偷偷乐,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,磨磨蹭蹭地爬上他的脊背。他背起她,继续朝前走。她暗恋了他五六年,第一次跟他这么亲近。他的手倒背过来扶着她。尽管隔着厚厚的军大衣,她仍然能够感觉到他的手在颤抖。听着他的喘息声,闻着他从大衣领口那里冒出来的汗味儿,她的心一阵狂跳。她幸福的闭上眼睛,希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。可是听见他越来粗重的喘息声,她心疼了,说:“放我下来!放我下来!”
他好像没有听见,继续吃力地朝前走着。她拼命扭动身子,两人一起摔倒在雪地上。他平躺在雪地上,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她看不清他的脸,但她知道他的脸色一定憋得黑紫。作为医生,她心里很明白,在海拔这么高的山上,什么东西也不拿,也相当于背着几十公斤的东西,她让他背着她走了这么远的路,实在太过分了!这哪里是爱,简直是虐待!她鼻子一酸,眼泪就涌了下来。
他问:“你能自己走了?”
她没有回答他,怕他听见她的哭腔。她站起来,把他从雪地上拽起来,然后转身独自朝山顶走。他无声地跟在后面。

旅途。 党益民 绘
厚重的云层开始蠕动,夜色粘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,山谷里传来狂风骇人的呼啸。转眼之间,狂风挟裹着冰雪劈面而来,世界像是被无形的大手撕扯成了碎片,在空中肆意抛洒。他们弓着身子,喝醉了似的顶风前行。她一个趔趄摔倒了,皮帽子被风刮跑了。她爬起来想要去追,他一把拉住她,把自己的棉帽扣在她的头上,系紧了帽带。他的头发被风揪起来,顷刻间钻满了雪粒,火炬一样挺立着。风太大了,无法继续赶路。他用胳膊围护着她,用身体抵挡着飞射而来的雪粒。他半拥半抱地将她拖到一处山岩底下,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突然“扑啦啦”飞走了,如同一片树叶在风雪中沉浮。她尖锐地惊叫一声,钻进他的怀里。他说:
“别怕,一只秃鹫。”
她声音颤抖地说:“听说秃鹫,专吃死人肉。”
“山那边有个天葬台,所以这一带秃鹫很多。”

山岩朝前倾斜着,好像随时准备拔腿逃走。山岩底有一片不大的空间,无雪也无草,遗留着牦牛粪和羊屎蛋,大概有牧民在这里避过风雪。他感觉她的身子还在发抖。她平时那么骄傲,现在却像小女孩一样胆小。昏暗中,他无声地笑了。她感觉到了他的笑。
“不许笑!”
他索性哈哈大笑起来。她气得用肩膀撞他:
“你这个坏人!”
她瞟了他一眼。微弱的雪光中,他的头发怪异地挺立着。看见他这副怪模样,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忙拨拉自己的头发,但怎么弄也弄不顺溜。于是,他报复似的说:
“我们脚底下这些骨头,不知是人的,还是牲畜的……”
她吓得跳了起来,声音颤抖着说:
“你再吓唬我,我可真生气了!”
他一本正经地说:“我吓唬你干啥,不信你看嘛。”
她把头扭向一边,不敢看脚下。她用脚摸索到没有骨头的地方,然后蹲下来,把身子缩成一团,泪水悄悄涌了出来。他没有发觉她在哭,站在最外面的地方,用身体替她挡着风雪。后来,雪渐渐小了,他刚想说“走吧”,远处传来了狼群的嚎叫。
“什么声音?”
“雪狼。”
“山上还有雪狼?”
“这一带雪狼很多,它们经常夜里光顾我们炊事班,偷吃我们的羊肉,但你不用怕,”他拍拍自己的腰间,“我带着枪呢。只要我开一枪,它们就不敢到跟前来了。”
他走出去看了看,扭头对她说:

“雪小多了,我们走吧。”
她坐在那里没动。
“我害怕,我不想走。”
“现在不走,一会儿雪下大了,更走不成了。”
“我们等天亮再走。”
“我们会冻死在这里的!快起来吧,我们走!”
“我不走,要走你走!”
“你怕狼是吧?有我在,它们伤不着你。”
“你说破天我也不走!”
他无奈地坐在她的身边。雪又渐渐大了起来,寒风将雪片旋进来,抛撒在他们脚下。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,只能再等等。
“你干吗不转业?”
他没想到她突然问这个问题。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,不知道她们的脑袋是怎么长的,天上一脚,地上一脚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,她这么一问,倒把他问住了。
“我干吗要转业?”
“你要是转业了,就可以天天跟老婆孩子在一起。”
他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,扭头去看她,她却看着外面,昏暗中,他只能看见她半个白净的脸,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情。
还没等他回答,她冷不丁又来一句:
“你的理想是什么?”

“我的理想?”他愣了一下,然后自嘲地说:“我的理想嘛,就是干好工作,不给父母丢脸,让家人过上好日子。哈哈,我一个被撤过职的基层小连长,还有啥理想?不过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好啦,我已经不习惯理想,我给你讲件真实的事情吧。有一年,我回家休假,在解放路上等出租车。那时候出租车刚兴起,不是很多。我等了很久,也没有等到。后来,有一辆三轮车停在我面前。说实话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是什么歌,我从来不坐三轮车,尽管付钱给人家,但坐在上面我会很不自在。但是那天,我手里拎的东西实在太多,就上了那辆三轮车。那人也没问我去哪儿,蹬起车就走。走了一段路,我才想起问他,我说师傅,你咋不问问我去哪里,就拉着我跑?他头也不回地说,你不就是要去安仁坊嘛。我感到很奇怪,说他怎么知道我要去那里?他说,我也是听村里人说的。我很吃惊,突然感觉那人的声音有些耳熟。我歪着脖子,极力想看清他的脸,问他是谁?他扭头朝我嘿嘿一笑。天哪,你猜咋的,是我的发小赵喜民!我让他赶快停下来,他说你坐着别乱动,在这里停车警察要罚款。我只好让他拉着继续往前走。他说他其实早就看见我了,只是不好意思到我跟前来,最后看见我实在搭不到车,才鼓起勇气把车蹬过来。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。他说村里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军官,全村人都为我高兴,后来我又找了个城里媳妇,更是全村人的光荣。他说他要供养两个娃娃上学,冬天干不成农活,就进城蹬三轮,除了自己吃喝,也能给娃娃们挣下点学费。”

“那天走到半道,我坚持让他把车停在路边。我说我从小就比你力气大,你坐上,我来拉你。他不让,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车抢到手。我蹬着三轮车,走在西安的大街上,他局促不安地坐在后面。他说你让我坐在后面,比我自己蹬车还要累。到了我家楼下,我拉他上去吃饭。那天,我亲手烧了几个菜,我们最后都喝醉了。我们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,一会儿笑,一会儿哭的。他说你当个军官不容易,找个城里媳妇更不容易,你一定要好好珍惜!第二年冬天,我休假回去,专门留心在火车站和西安的大街上找他,却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后来我回了一趟老家,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他得了肝腹水,却舍不得花钱看病,躺在炕上硬抗着,后来肚子越来越大,就死了……唉,在这世界上,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。我们常年呆在高原修路,远离家乡和亲人,尽管也很苦,但与我的发小相比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如果不出来当兵,也许会跟他一样,连看病的钱也没有。所以我不能让父母失望,不能让村里人失望。这也许就是我不愿意转业的理由……”

外面的风小了,但雪仍在下着。
他说:“好啦,不说了。风停了,我们走吧。”
她问:“狼还在吗?”
侧耳听了一下,说:“狼不在了,跑走了。”
她侧耳听了听,确认外面没有狼后才说:
“那你等等,我去去就来。”
“你上哪儿去?”
她没有回答,站起来朝外面走。他明白了,冲她的后背说:
“别跑太远了。”
过了一会儿,不见她回来,他有些担心,但又不好出去找她,只能等着。又过了一会儿,还是不见她回来,他沉不住气了。
“黄医生,黄医生!”
没有听见她的回答。他慌忙站起来,跑到外面的雪地里,看见不远处有团黑乎乎的东西。他又叫了两声,不见答应。是不是晕倒了?他急忙跑过去。她果然歪斜地倒在雪地里。他慌了手脚,将她抱回山岩下。她紧闭着双眼,双手冰凉,头发上粘满了雪粒。他知道这是因为高山反应引起的暂时性昏厥,过会儿就会好的。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她,用自己的脸去温暖她已经冻僵的脸……
他感觉到两张脸之间有股热热的东西流淌。他慌忙移开自己的脸,她却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。他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血管里奔流。但他还是轻轻取下环绕在脖子上的胳膊,扶她坐好。
“你可醒了,吓死我了。”
她没有说话。
“解个手嘛,你干吗跑那么远?你看多危险!”
她轻声地啜泣起来。
他装着没听见,站起来说:“好啦,咱们走吧。”
他把她拉起来,走进雪地里。外面的积雪很厚,没过了小腿。他们一前一后吃力地向前走着。他走在前面,说:
“你踏着我的脚窝走,会省力些。”

她很听话,踩着他的脚窝走。走着走着,她猛一抬头,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团萤光晃动,惊诧地问他:
“山上怎么会有萤火虫?”
他抬头一看;“不好,是狼!”
她尖叫一声。他伸开手臂护住她,伸手去腰里拔枪,狼群已经蹿到了跟前。他一面上膛,一面说:“你快蹲下!”
话音刚落,一只狼率先扑了上来,他把脑袋一歪,那狼没有咬住他的脖子,却叼住了他的大衣领子。他的手已经冻僵,扣不动扳机。他顺势用力一推,将狼推出几米远。这时,另一只狼腾空一跃,扑向后面的她。他朝着狼的肚子扣动了扳机,只听“叭”的一声,那只狼无声地栽倒在她的跟前,其余的狼四散而逃……
他们跌跌撞撞地退回到刚才避风的山岩下。群狼尾随而至,蹲守在外面的雪地上,一阵阵“嗷嗷”地嚎叫着。他朝最近的一只狼打了枪,没有打中,但把狼群吓跑了。但它们并没跑远,而是伏在不远处的雪地里,一直虚张声势地嚎叫。过了一会儿,有三只狼见没有危险,肚皮贴着雪地一步步走过来。手枪里还有五发子弹,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。那三只狼很狡猾,并没有扑上来,而是在距离他们七八米的地方,“蓦”地一起调转身子,用后爪疯狂地刨起地上的积雪,雪粒飞溅,一时遮住了他们的眼。他知道狼群马上就会进攻了,他朝外面开了一枪。狼跑开了。但它们并没跑远,其他狼慢慢围拢过去,好像要开会研究进攻方案。

子弹还剩下最后四发。即使是神枪手,也不可能用四发子弹射杀十几只狼。但是与狼对峙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他用身体挡着瑟缩发抖的她,右手端着手枪,左手从衣兜里摸到了打火机。狼怕火,只能用火来对付它们了。他掏出打火机,“噗”地打燃,四周“哗”的一片通明。狼群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光吓了一跳,倏地逃走了。
打火机腾起蓝色的火苗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。她颤声问:
“狼走了?”
“走了。但它们没有走远,就在附近。”
“是不是打火机一灭,它们就会回来?”
他心里说“是啊,没有火光,它们就会回来”,可是他不能说。蓝色的火苗渐渐变成了桔黄色,眼看就要熄灭了,他得赶快想出别的办法。他担心耗尽打火机里的汽油,只好让它暂时熄灭。眼前顿时一片漆黑。他看不见外面的情况,但他能够感觉到狼群正在一点点地靠近。他飞快地脱下大衣,从刚才被狼撕破的领口开始撕,撕下布片和里面的棉花,然后用打火机点着。一股卡几布的焦糊味儿弥漫在四周。狼群绝望地在外面嚎叫。可是他的大衣很快就要烧完了。她脱下自己的大衣,递给他。他说:
“不行,没有大衣,你会冻死的!”
“女人比男人更耐冻。”
“对了,我有办法了。”

借着微弱的火光,他从地上捡起一根骨头。那骨头有些年头了,很容易就被点燃了。她颤声问:
“不会是人骨头吧?”
他不敢肯定,但他安慰她说:
“不是,是羊骨头。”
她拍拍胸脯:“吓死我了,我还以为是人骨头呢。”
地上的骨头不少,他一根一根地捡着,烧着,幽蓝的火苗在黑暗中飘忽跳动,狼群一直不敢近前……
天亮了,雪也停了。狼群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了,大雪甚至已经抹平了它们留在雪地上的足迹,好像它们根本就不曾来过。他们从山岩下走出来,艰难地向山顶走去……
未完待续

作者简介

党益民,陕西富平人,诉讼法学研究生,武警西藏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。2次荣立二等功,11次荣立三等功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喧嚣荒塬》《一路格桑花》《石羊里的西夏》《阿宫》《父亲的雪山,母亲的河》《根据地》《雪祭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用胸膛行走西藏》《守望天山》等10余部文学著作。《一路格桑花》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,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;《守望天山》改编成电影和歌剧。作品曾获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、北京文学奖、徐迟文学奖、柳青文学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是什么歌,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。
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版 党益民 著
授权发布
限 时 特 惠: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,一年会员只需98元,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
站 长 微 信: qihangxm1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