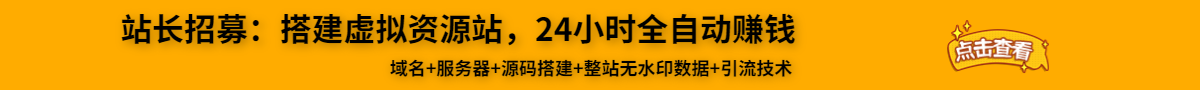做早餐时,听见楼下那户的小孩子在朗读古诗,空气里顿时像迎风抖开了一匹绸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杳杳地传来。可惜今日中秋,白露早过,已经是莺鹃蝉蛩诸声定静的时节。不过听孩子用他脆生生的嗓音念着蒹葭蒹葭,倒是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,小时学课文,知道蒹葭就是芦苇,毛苌的《诗疏》里有阐述,“苇之初生曰葭,未秀曰芦,长成曰苇。苇者,伟大也。芦者,色卢黑也。葭者,嘉美也。”读来复杂蒌蒿怎么读,简而言之蒹葭就是初生的芦苇,不过正如古人在《春秋元命苞》里说的那样,露能润草,霜以杀木。一年之中到了中秋这个日子,露从今夜白,天地也该勃然变色,蒹葭也该由盛转枯喽。

芦苇
真是令人敬畏啊,大地与季节的驯良,各种植物看似都活在自己的来回里,实际都蕴藏于法则之中,丝毫不乱。广袤无垠的天、不可期的朝阳晚照、杂乱的荒蛮之中,其实充满了温顺,就像一到了秋天,哪怕水域再空旷,但一定有一枝芦苇,正在某处悄悄地爆出一点苍白,迎合着响亮又爽利的水声。就是这样,一切该长的,就非得这么长不可,令人吃惊的时令,囫囵霸道之中,有着幽秘且从容的秩序。

作为禾本科植物,芦苇所在家族血统之正,大概无需赘言,在物候志狗尾草篇里边,我曾有过阐释。但芦苇的确是辨识度太低,光是跟它相似的就有芦竹、芦茎、南荻、爬苇、芒草、丝毛芦、白茅草,分分钟能把人绕晕。
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芒草,记得有一回,我在香港大屿山,见过很大片的,满眼的米黄色,而且芒草猬集生长的地方,通常都很纯粹,据说是因为芒草在地下的根茎很长,又长得纵横交织,所以挤走了其它植物。只在少数情况下,能见到一种野菰,它寄生于芒草根部,自身不进行光合作用蒌蒿怎么读,全靠芒草的营养而活,花是粉紫色,长得有点儿像烟斗,所以又叫“烟斗花”,在民间,是一味有名的蛇药。日本也有,他们叫“南蛮烟管”,我以前到奈良万叶植物园时,正是野菰开花时节,园方还会特意贴告示周知,可见日本人对这种全株皆可入药的寄生草本,很有好感。

大屿山芒草
当然,就算芦苇跟芒草长得再像,对于大才子苏轼来说,也不是什么难于辨认的事儿,他的那首“芦笋初似竹,稍开叶如蒲;方春节抱甲,渐老根生须;不爱当夏绿,爱此及秋枯;黄叶倒风雨,白花摇江湖;江湖不可到,移植苦勤劬;安得双野鸭,飞来成画图,”简直是我所见过的描绘芦苇之最风韵最生动。

但是天知道苏轼是不是因为好吃,才对芦苇那样熟悉。譬如他还有首妇孺皆知的吃货诗: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其中的蒌蒿,郭璞有注,“蔏蒌,蒌蒿也,生下田,初出可啖,江东用羹鱼。”在我的老家益阳,则叫泥蒿,凉拌、清炒、煮鱼或炒肉,是怎么都宜,吃口还满是驯不服的水气。吾乡有句民谚“正月泥,二月蒿,三月四月当柴烧”,这种多年生的宿根草本,因根系发达,能匍匐于地下近二十厘米,因此它直立于地上的茎,一遇着高温就疯长,老化得也就非常快。

蒌蒿
至于苏诗里的“芦芽”,就是今天的芦笋,天门冬科的植物,常被误作芦苇的幼苗。芦笋在古代是著名时鲜,用以同河豚共烹煮,说起河豚这味美食吧,也真是一言难尽,我曾在杭州吃过鹅肝酱河豚片,并不觉得有多美味。但据说在宋代,人人“拼死吃河豚”,一尾鲜河豚时价可卖至千钱。尽管这种内脏含有剧烈神经毒素的鱼,人畜误食后,重则可至死亡,但人类在吃这件事上,可早就穷奢极欲了。
好在世间之物,往往是“卤水点豆腐,一物降一物”,后来据李时珍考证,芦笋可解河豚及诸鱼蟹毒,从那以后,贪恋河豚之美而又惴惴不安的吃货们,才算有了一剂定心丸。只是,再回头看看苏轼的诗,不免就会觉得惊恐,将芦笋与河豚并之,是巧合?是先知?还是神迹?

芦笋
回到芦苇,有一年,我到黄草采访一位草药郎中,他最喜芦苇,家里扫帚枕头刷子垫子全是芦苇做的,黄草镇在东江湖的一个岛上,四周环水,所以有大片的芦苇荡,那儿是水鸟们挚爱的栖息地,秋风一起,苇叶失去叶绿素,就会变成黄白色,这时,密集的芦苇丛就成了水鸟们隐蔽的王国,最常见的两种水鸟,我认识,大麻鹭和黄苇鳽,毛色多以黄黑白三色为主,乍一看都跟环境相融,它们平日就藏在芦苇丛里,以各种水生小动物为食。一旦遇到敌情,马上呆立不动,试图将自己伪装成枯黄的芦苇。
那老郎中从医四十多年,每天都风雨无阻背个蛇皮袋出门采药,所以每天都会跟那些水鸟照面。有时累了,就坐水边上,折一枝芦苇,放到嘴里嚼,跟我说他这几十年里的故事。

水鸟在芦苇丛中
“我本来不愿意学的,但我师父没有后人,他偏偏看中了我,觉得我骨骼清奇又不重钱财,是学医的好材料。”老郎中就像大部分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人一样,动荡和苦难,在他们的命数里一样没落下,因而生存意识格外强烈,就想好好挣钱活下去。而草药郎中,这是个情义比天高的行当,他一开始真不大愿意。
后来,他到师父家里,见屋中到处码叠的线装本医书医案,闻着空气中萦绕不去的苦清气,突然感到浑身清宁,几十年后,他是这样潦草地解释自己下定决心的原因,全赖草药名字好听,比如半夏、车前子、当归,川贝、墓头回、益母草、泽泻、穿心莲、夏枯草、黄连、乌头等等,一个个听起来像个妖怪;还有那些盘在一起的干蛇和穿山甲、蝉蜕,他也喜欢看。

芦苇丛中的秧鸡
那年头,岛上还没有公路,尤其是上山采药的小路,又陡又窄,他每天跟着师父背个竹筐篓,攀住路边的乱藤和巨石往上爬。他们拿着镰刀和锄头在悬崖峭壁上寻找那些能治病的草药,累到大汗淋漓时,就找个有风的地方歇会儿,顺便将落进草鞋缝里的小石子抖出来,有时,师父会挑些筐篓里的草药放到嘴里,咬一小口,嚼一嚼,吐出来说:“徒儿啊,你尝尝,它们虽然都是无根藤,但味道不同,甘而微苦这支能入药,又涩又苦这支入不得的,因为涩苦的这一支是寄生在马桑这种毒草上的,病人用了会中毒。”

如今,师父已故去多年,老郎中也日渐老迈,此生波澜壮阔,也免不了日薄西山,他眼下很想收个徒弟,但就是遇不上合适的后生,“行医最最重要的就是心慈,做郎中的,谁来请都要去,有钱没钱都要去,这是一个医者的根器,丢不得,但现在的人,多数不认这套了。”
平日,没有人来看病时,老郎中就坐在木格窗边,往下望碧绿的东江湖水,他喜欢看船在水上行驶时,波纹浩浩荡荡的感觉;也喜欢看那漫天遍野的芦苇,一入秋,就开出毛茸茸的芦花,虽然那并非芦苇真正的花,而是它的果实,自古人们说芦花芦花,其实皆是虚妄;唯有果实,才是沉甸甸的真实。想来,吴承恩大概是早就洞悉了个中奥秘,所以在《西游记》里写“八百流沙界,三千弱水深;鹅毛飘不起,芦花定底沉。”

芦花
那一瞬间,我突然有点儿明白,毕生与草木为伴的老郎中,为什么会那样喜欢芦苇,能以草的底子,长出花的颜色,这应该需要不一般的心性与格局吧。它那苍白如一席罽毳的“花”,是那样子平静地长在荒野长在水边,一如它的茎和嫩花序的味道,浅浅的淡淡的鲜香,有一种脆生生的草清气,但人在尝它们时,无一例外地都会忘记那些饱食的终日,经过了它身体里那一汪汁液的洗礼,人的嘴里也似流过了一条河,寂寂清清,顺着喉咙一直淌到心底,直到那时,日影流光,纷乱红尘,都化成了一段清平水意,这才是一个人活到终点时的滋味吧?

古人说“最是平生会心事,芦花千顷月明中”,如果味蕾能辩出三千六百种酸甜苦辣,而芦苇无疑是最后一种滋味,不酸不苦不辣也不甜,然而一切又都藏于其中,所谓集众味之所成,才是淡然平浅的涅槃之味。
(图片来自网络)
回顾往期可点击:
限 时 特 惠: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,一年会员只需98元,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
站 长 微 信: qihangxm102